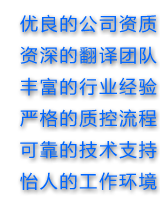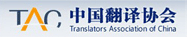洛阳翻译公司-我合作过的翻译
我这一生当中,合作过的翻译真是数不胜数,我也不可能一一写到。他们有的已经不在上海了,还有的已经去世。而有些人,则成了终身的朋友。
首先是我的同事,从一九五七年就在一起工作的叶琼。她既能译英文又能译俄文。她可能是跟我合作最多的了,因为有些不是她翻的本子厂里也常常会让她做编辑。她工作认真,作风朴实,她懂的问题,会跟你讲得很透,她不懂的问题,决不会不懂装懂,所以跟她合作,你会感到很放心。特别是在搞突击任务的时候,经常是我们两个人一组,她做编辑,我做口型员,翻译翻好的剧本,由我们按口型修改好,就直接送到棚里去录音了。记得那是在一九六一年,我们译制日本片《松川事件》。整部影片一共二十四本(等于两部电影),为了支持日本共产党的活动,厂里要求我们五天搞好。真的是夜以继日连续作战。我们两个人对着对着口型都睡着了,片子还在那里放着,忽然醒过来看看剧本上,不知道都写了些什么,就像蚯蚓在爬。等到整个影片录完,那些男同胞一个个已经困得等不到回家,就在阳台上横七竖八地睡上了。
她曾翻译过前苏联片《不同的命运》、《苦难的历程》、《雁南飞》等,与孙道临、刘素珍合作翻译过《春闺泪痕》、《琼宫恨史》,还独自翻译过《铁道儿童》等内片。她上世纪八十年代独自翻译或与人合作的有美国片《苦海余生》、《噩梦》、《非凡的艾玛》、《苔丝》、《尼罗河上的惨案》、《凡尔杜先生》、《水晶鞋与玫瑰花》等等。由她编辑的影片就更数不清了。
她离厂已经二十多年了,有时想起当年翻得不恰当的句子,仍不免耿耿于怀。像《雁南飞》中有一句话说“大雁排成人字形”,她说:“俄文中哪有‘人’字,还是应该按原文译成舰队形。我想起来就觉得遗憾。”
我们厂还有一位老翻译—法文翻译徐志仁。老徐既能法译中,又能中译法。一般来说,从外文翻译成中文是比较容易的,你只要看懂了外文的意思,用你所熟悉的母语来加以表达,总要方便一点。如果反过来,让你用你不那么熟悉的外文来表达就困难多了。
老徐翻译的《虎口脱险》,真是异常精彩。如果不是老徐的台词翻译得那么有味儿,演员也不可能表达得那么生动、诙谐。他把口型掌握得那么恰到好处,好像口型是为台词而设置的。有人把《虎口脱险》看过无数遍,记住了尚华、于鼎,却不一定知道它的翻译是谁。这真有点不大公平。
我跟他合作的,除了《虎口脱险》,还有讲贝多芬生平的《不朽的情侣》。
我除了在厂里跟他合作,在电视台译制部也请他来翻译过《缉私行动》以及河南电视台委托我们译制的法语片《无辜者》等等。
可惜,他已因病去世了。
赵津华与朱实两人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借到我们厂搞内参片开始与我们合作的。赵津华生于日本,九岁才回国,又在日本学校读的小学,所以比较了解日本的风俗习惯。而且她又非常聪明,也非常努力,很快就掌握了搞译制片的规律。她曾和朱实一起翻译过很多日本片如《战争和人》、《啊,军歌》、《啊,战友》、《日本最长的一天》等等。
朱实是台湾人,从小到大都是在日本学校读的书,等于半个日本人,是个日本通。
“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口了大量日本片,由我担任译制导演的如《远山的呼唤》、《雾之旗》、《啊,野麦岭》等,翻译的剧本都出自赵津华之手。我们译制《我两岁》的时候,她已经调到香港去工作了。那些天正好碰到她在上海休假,我一听说马上到她家把她“抓”了来,让她翻译了《我两岁》的剧本。那时候他们翻译剧本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完全是义务劳动。
朱实曾翻译了《金环蚀》、《啊,野麦岭》(续集)、《白衣少女》。我到电视台译制部以后,他又帮我们翻译了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的锁链》。
至今,他们二人仍然是我经常来往的朋友。 (48)